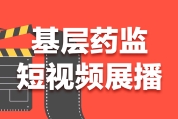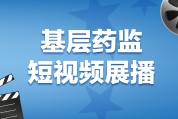罕见病药物可及要跨过多少关
- 2025-10-09 13:41
- 作者:李易真
- 来源:中国食品药品网
中国食品药品网讯(记者李易真) 9月20日,国家医保局宣布,2025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以下简称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专家评审工作已结束。
“在商保创新药目录评审过程中,其审评规则明确,优先考虑已经纳入地方惠民保和商业保险的罕见病用药。”同日,商保创新药目录专家组成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孙洁在2025第十四届中国罕见病高峰论坛的分论坛上如是表示。
“尽管越来越多的罕见病药物进入中国市场并被纳入保险目录,但我国仍有上千万名罕见病患者面临无药可用或有药用不起的困境。”蔻德罕见病中心创始人兼主任、全国DMD患者家庭联盟管委会主任委员黄如方说。在我国,罕见病药物的“可及之路”在药物研发、临床应用和支付保障等环节仍面临重重挑战。
探索药物研发“无人区”
对于陈君(化名)而言,给9岁的儿子皮皮洗澡是一项艰难的任务。皮皮在1岁时被确诊患有佩梅病,这是一种罕见的X连锁隐性遗传病,主要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髓鞘发育。由于身体无法自主支撑,皮皮洗澡时必须完全依靠陈君。
不仅如此,更令陈君痛心的是,随着疾病进展,皮皮的智力和语言水平也在逐渐倒退。
据研究报道,中国约有2万名佩梅病患者,但目前全球尚无针对性的治疗药物上市。
“罕见病药物的研发较之其他新药更为艰难。”渤健亚太区总裁丁伟波说。传统药物研发在业内有所谓的“双十定律”,即研发一款新药平均要耗时10年、投入10亿美元。但罕见病药物的研发,则被视为勇闯无人区。
以脊髓性肌萎缩症(SMA)为例,科学家早在1995年就找到了致病基因,但直到2016年,全球首款对因治疗药物诺西那生钠注射液才在美国获批,中间经历了长达二十多年的艰苦研发历程。
佩梅病治疗药物的研发面临同样的挑战。尽管已知佩梅病发病原因,但时至今日,像皮皮这样的佩梅病患者仍只能依赖家人的全程照顾,无药可治。
阿斯利康全球高级副总裁、罕见病药物临床开发、注册及患者安全负责人Gianluca Pirozzi表示,目前约80%的罕见病属于遗传性疾病,其发病机制复杂且类型多样,医学界对大多数罕见病的认知有限。因此,在基础研究阶段,很难通过动物模型准确模拟人类疾病的病理过程。而在临床试验阶段,由于罕见病多在儿童期发病,罕见病患者人数少且分布较散,儿童受试者的招募也更加困难。
“罕见病药物研发在转化阶段面临的最大挑战并非单个科学难题。”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眼科研究所所长沈吟指出,其关键在于如何在小样本、异质性强且证据链要求高的前提下,实现安全、有效和可及三者的闭环。
她表示,当前患者信息、药物疗效、真实世界数据等分散在不同医院、科室或科研团队,且数据的质控标准和随访周期不统一,导致有效的数据难以整合与共享,延长了从靶点发现到临床转化的研发周期。
据介绍,在“无人区”探索过程中,全球罕见病药物的研发策略从“缺什么补什么”的单靶点替代模式,向以临床疗效为导向的综合干预策略发展,以期更高效、更系统地应对复杂疾病的治疗需求。
跨越临床使用多重障碍
然而,即便药物成功研发并获批上市,要想实现对患者可及,还必须实现临床使用。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当前我国罕见病临床诊疗体系仍面临疾病认知不足、诊疗资源不均、临床使用意愿低等多重障碍。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儿科学系主任、同济儿童医院院长罗小平指出,罕见病通常涉及多个器官系统,复杂多样的临床表现给诊断和治疗带来极大挑战。同时,我国各地诊疗资源分布不均,一些偏远地区或基层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缺乏罕见病相关的医学知识和诊断能力,进一步加剧了误诊、漏诊以及反复转诊的现象。
丁伟波表示,诊断的延迟不仅使患者错过最佳治疗窗口,也大幅缩短了药物发挥价值的周期。他以SOD-1基因突变的渐冻症为例,患者从出现症状到首次就诊平均需8至9个月,而从首诊到确诊还需约11个月,平均辗转2至3家医院,整个过程超过一年半,而渐冻症患者发病后平均存活期仅3至5年。
除了诊断环节的挑战,医疗机构在罕见病药物使用方面的积极性也受到现行医保支付政策的制约。2025年8月,国家医保局发布《医疗保障按病种付费管理暂行办法》,按病种付费已基本覆盖全国统筹地区。
然而,有专家坦言,在这一“按病组打包付费”的机制下,罕见病由于患者数量少、个体差异大、资源消耗高,常常面临“难以精准入组”或“入组即亏损”的困境。他表示,DRG分组权重是基于整组历史平均费用来确定的,但罕见病的费用结构往往偏离常规,导致医保结算金额远低于实际诊疗成本。
记者在会上获悉,一家知名三甲医院收治了一名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患者,按照DRG病组结算方案,其支付标准约1.3万元,而实际医疗总费用却高达10万余元,医院单例患者亏损超8万元。
上述专家指出,尽管国家和部分地区设有“特例单议”机制,为因住院时间长、医疗费用高、新药耗新技术使用等不适合按DRG/DIP标准支付的病例提供补偿,但在实际操作中,不同地区的医疗机构在专家评审和通过率上存在差异。这种结算压力使得不少医疗机构在收治罕见病患者时“望而却步”,进一步加剧了罕见病患者就医的困境。
破解天价药“最后一公里”
罕见病治疗药物的高昂价格,成为患者在临床治疗阶段面临的又一道“高墙”。由于患者群体规模小、市场需求有限,制药企业为收回研发成本,往往将药品定价较高,使得不少药物成为普通家庭难以承受的“天价药”。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医药卫生管理学院院长姚岚介绍,在我国各地现有的罕见病保障政策下,患者需要自付部分仍然大大超出其支付能力,对大多数家庭而言无疑是沉重的负担。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国家基本医保虽在罕见病保障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但其定位是“保基本”,面对罕见病药物的高额费用,仅靠基本医保难以覆盖所有相关药物。
《2025中国罕见病行业趋势观察报告》显示,目前仍有58种已纳入罕见病目录的疾病对应的65种药物未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其中33种罕见病的全部治疗药物均不在医保报销范围内。这些药物年治疗费用甚至高达几十万元到上百万元,普通患者家庭难以承担。
在定价机制方面,丁伟波强调:“罕见病药物的定价并非针对患者个人,而是针对支付端的。”他认为,罕见病药不应该、也不能主要依靠个人和家庭支付,商业保险应在支付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与政府医保、慈善救助等协同,构建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
然而,商业保险在覆盖罕见病时也面临内在挑战。宸汐健康医药事业部总经理余晶逸指出,罕见病多为遗传性,患者通常一出生即患病,这与保险基于“大数法则”的设计原则相悖,导致两者“天然匹配度”不高。
“事实上,约90%的渐冻症患者并非家族遗传,从概率上来讲,每个人都有可能与罕见病相关。”在丁伟波看来,将渐冻症这类关注度高、社会意义重大的罕见病纳入商保,不仅能提升公众对于商保的购买意愿、扩大保障资金池,也为保险企业提供了践行社会责任、提升品牌美誉度的机会。此外,由于罕见病发病率低且风险可预测,符合商保的精算逻辑,有助于实现业务的可持续性。
作为政商融合的普惠型保险,“惠民保”在地方层面被寄予厚望,成为不少患者跨过创新药支付门槛的重要支撑。《中国创新药械多元支付白皮书(2025)》数据显示,2024年惠民保特药责任中,罕见病患者的人均药品赔付金额达20万元/年。尽管如此,仅依靠“惠民保”仍难以完全解决罕见病患者家庭的用药负担。
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以基本医疗保险为基础,补充医疗保险、医疗救助、商业健康保险和慈善等其他保障模式协同发力的“1+3+N”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然而,在专家看来,这一体系在罕见病保障方面仍需进一步完善。
姚岚认为,商业健康保险作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作用是分担患者较重的疾病经济负担,包括罕见病药品费用的分担,同时也需相关配套政策支持其有效良性的运行和发展,以保证其可持续。同时在罕见病领域更要发挥慈善的费用分担作用,通过多元化费用分担的形式解决罕见病疾病经济负担的问题。
在地方层面,江苏、浙江、青岛等地已率先开展多种形式探索,如建立省级罕见病专项基金、探索“费用分摊”机制等,为破解支付难题积累经验。
在此基础上,孙洁进一步呼吁,国家应在总结地方经验的基础上,适时设立国家级罕见病专项保障基金,建立多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并通过财政专项拨款、社会慈善捐赠等多元化渠道,切实打通保障的“最后一公里”,让更多罕见病患者能够用得上药、用得起药。
《中国医药报》社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使用。
(责任编辑:宋莉)
分享至
右键点击另存二维码!
-
相关阅读
-
为你推荐